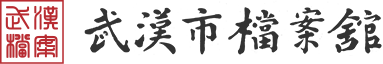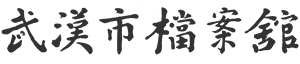关于对美国数字时代版权法修改的几点思考
发布时间:2015-09-14 00:00 来源:市档案局办公室
“得到机油的是响轮”
——关于对美国数字时代版权法修改的几点思考
作者:艾普芮尔·库奇·麦凯
来源:中国档案报

艾普芮尔·库奇·麦凯
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密歇根大学
本特利历史图书馆法律专家
相信中美两国档案工作者向他人介绍自己的职业时都会有共同的困惑,即如何让他人迅速了解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在美国,我遇到的许多人并不熟悉档案工作。他们会疑惑地问我:“什么是档案工作者?”有时我会说,我们的工作类似博物馆管理员,只不过档案工作者的管理范畴不是那些艺术品和三维作品,而是文档;有时我会说,我的工作就像图书管理员,只不过我关注的是那些未经出版的、独一无二的、珍稀的历史证据。我的很多新朋友常常会问我,本特利历史图书馆是不是会把全部馆藏都做数字化处理?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决定某件档案能否被数字化并传至互联网之前,需要经过审慎的分析和研究,档案资料和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版权因素都应在考虑范畴之内。比较常见的情况是,美国现行的版权法禁止我们将那些有趣且珍贵的档案材料公布上网。因版权法有明文规定,作者和艺术家有禁止将其作品公之于众的权利,尽管档案馆明确知道档案的创作者及其联系方式,仍无法利用。这条规定虽然对政府的公文档案并不适用,但是尤其适用于那些由个人或私人机构创作或产生的档案。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也是针对私人档案的。
美国现行的版权法于1976年颁布,其中规定,作者对其作品在创作之初即享有著作权。即使作品并未出版,作者也无需作出版权公告或向政府申报版权,只要把作品记录下来并存储在一种有形的介质之中(如纸、布或是电脑硬盘上)。拥有著作权意味着作者可以禁止他人对其作品进行复制、出版、公布、展示等行为。
如果有人未经作者许可,对其作品进行复制、出版或展示,法律规定作者可将侵权者告上法庭并追缴相关经济损失。一旦被诉诸法庭,被告可以作出如下的辩护:尽管我复制了你的作品,但法律规定从我的职业角度和特殊身份来讲,这是合理的,因此不能让我赔偿因复制作品所带来的损失。
目前,关于图书馆和档案馆里保管状况不佳且呈恶化趋势的档案,有一些特殊的复制规定。但这些规定制定得较早,从前复制档案的方式仅限于复印机和缩微胶片,因此这些规定在现在看来有些不合时宜。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生活中历经的技术变革要比修订法律快得多。
举例来说,为了对那些保存现状不乐观的档案进行保护,档案馆可以对其进行复制,但复制形式仅限3种——缩微胶片的底片、打印件、服务或利用副本,当然这是以微缩胶片形式保护档案时期的标准,这个标准已经过时了。现如今,档案的保护方式更倾向于转化为数字副本,很难想象在数字化保护过程中,只能以3种形式来开展保护工作。
如果不将已数字化的档案上网提供利用,这本身就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和不充分使用。尽管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的大部分馆藏内容并非由那些要通过自己作品来盈利的个人创作,但版权法依然要求我们在公布每件档案之前,都要想方设法取得版权所有者的同意。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有本旧信件集,都出自同一个人之手,那么找到作者本人获得他的允许来开放信件还并不算难。收信者是一个人,但写信的人却是五花八门,每个人都对自己写的信享有著作权。如果档案馆不想成为被告,则要在公布信件集之前分别去征求每个写信人的意见。
所以说在很多情况下,现行版权法已经过时了,对于那些正在积极开展档案征集项目,并向公众提供信件、日记等私人档案的档案馆来说,版权法甚至成了“障碍”。很多美国人都意识到了这点,并开始思考如何修订该法。2013年4月24日,立法委员会开始对版权法的全面修订进行审查。修法是个大动作,有时也是令人望而却步的。因为在起草一部新法之前需要征求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他们的意见会左右有关法律内容的变更。档案馆和图书馆关注作家和艺术家的权益,但有时候却与一些大型电影发行商、音乐出版公司的意见相左。商业机构都以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并不会考虑到自身关于修订版权法的建议会对档案馆和图书馆产生哪些不利影响。这些大型公司对立法者的影响很大,不言而喻,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娱乐业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美国档案工作者仍决心加入这场论战,希望在修法过程中充分采纳档案馆的建议。在此之前,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美国档案馆的管理和协调机制。
在美国,收集历史档案资料的机构很分散。美国国家档案馆是联邦机构,55个州分别设立了自己的档案馆,各州州长对本州档案馆行使领导职能。另外,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也设有档案馆,他们都是独立于州和联邦档案馆之外的,换言之,这些大学档案馆对其所属大学校长负责。还有一些是非盈利机构或商业机构建立的档案馆。上述档案馆在享有自主的管理权和支配权的同时,都必须遵守版权法。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美国各种不同类型档案馆都保存有私人产生的档案。
也就是说,在修订版权法过程中,如想明确有力表达档案工作者的观点则需各方的共同努力。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AA)就是汇集各类档案机构声音的最佳平台,目前该协会有6000余名会员,旨在为档案工作者提供教育和信息服务。SAA通过发起讲座和辩论、主办研究杂志等方式,将个人会员的诉求和意见收集汇总,并在国际舞台上进行表达和呼吁。
下面我要列举美国档案工作者在助推版权法现代化进程中的3种途径。
首先,我们开展了有关研究。在过去的数年内,不少人作了关于向档案资源的版权持有者征询是否能够开放的调查,研究证明这其中的难度的确不小。比如,密歇根大学的一位女同事达尔马·艾克蒙,为了学术研究,需要将乔恩·科恩医生关于艾滋病的研究成果数字化,为此,她需要将研究成果中所有13381项条目创建元数据并明确版权界定。
实际上,这不是我们通常的做法。一般来说,我们只在文件夹级建立元数据,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对更多数量的档案卷册进行著录并提供利用。但是为了将有版权的内容上网,根据现行版权法要求,艾克蒙需要获得每个条目版权持有者的许可。这无疑增加了项目的投入。最终,艾克蒙成功联系到的大多数人,他们都同意将自己的信件免费放在网上。这些档案材料的创建者根本没有想过通过自己的作品来盈利,这也是档案文献与商业界最大、最重要的界限。
档案工作者对艾克蒙的研究成果并不奇怪,因为这是我们的共识,但是这对于其他非档案行业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立法者格外重要。作为档案工作者我们常常陷于努力开展我们的工作与版权法之间的矛盾,需要将此事用恰如其分的语言向立法者作出解释。
第二,我们通过创建行业最佳实践范本来影响立法进程。通常来讲,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会对相关群体的职业惯例进行考量。在涉及版权法的范畴内,法院通常会对某个行业的实践经验和行为来裁决某些具有版权材料的再次利用是否属于“合理使用”。档案工作者、图书馆管理员、纪录电影制片人、舞蹈老师、诗人、媒体等群体都会形成各自的团体意见,从而帮助法庭裁决什么行为是可以接受的、符合道德伦理的。
比如我参与起草的“善意地将数字化后的未出版材料上网”文本,就对数字化后的材料和作品集上网的法律和道德合理性进行了总结。这份文本还指出,如果有人对网上发布的某些内容提出抗议,可以采取立即“拿下”的措施,这样做可以减少对著作权拥有者利益的损害。同时,该文本还列出了几类不适合上网的内容。我们希望这些最佳实践的范本最终在法庭审理中作为代表档案界观点的重要证据,帮助档案馆证明他们没有违反法律和道德进行档案开放活动,而是遵循行业的标准和实践。
第三,档案工作者努力把关于修订版权法的想法直接反馈给SAA下设的知识产权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关注法庭和立法过程中所有有关版权的消息,并负责向SAA领导层作出政策方面的建议。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曾就版权法应作出哪些改变,特别是进行大规模数字化方面征求过公众意见。该委员会得知消息后,起草了一份档案工作者关于立法改变的建议。SAA领导层通过了这项草案,后由SAA主席签署,并转交给政府的相关官员。
美国的图书馆管理员远远多于档案工作者,所以有时档案工作者也会向图书馆管理员发出倡议,请他们代表大家共同的诉求。但在上述关于在网上开放作品集方面,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立场却有所不同。在美国有一句谚语:“得到机油的是响轮。”档案工作者就要做响轮,我们需要外界了解版权法应作出哪些调整,从而允许我们将馆藏中有价值的资源数字化并提供有效的利用。通过进行研究、制定最佳实践文本、组织合力宣传3种方式,希望我们获得让“车轮”跑得更快的“机油”——一个现代、高效的版权法,能让档案资料在数字时代获得最大应用。
杨太阳 译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8月13日 总第2798期 第三版

![]() 办公室电话:027-82812716
办公室电话:027-82812716
![]() 值班电话:027-82834953(夜间、节假日)
值班电话:027-82834953(夜间、节假日)
![]() 档案馆查阅咨询电话:027-82812709
档案馆查阅咨询电话:027-82812709
![]() 展览参观咨询电话:027-82784374
展览参观咨询电话:027-82784374
Copyright © 2020 武汉市档案馆 版权所有 湖北省武汉江岸区怡和路59号
鄂ICP备19019621号-1
 鄂公网安备 42010202002201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202002201号


读档

武汉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