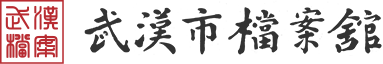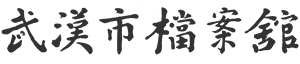散文:七 月
发布时间:2017-02-20 00:00 来源:
积玉桥地铁站出来,有长长的一段路到都府堤。
沿途会遇到不少上班的人,拎着热干面或者包子,匆匆忙忙的样子。太阳打在身上,汗吵吵嚷嚷地往外涌,人一蹶不振。到七月的尾巴,我渐渐熟悉了这条路,习惯了在都府堤的生活。
然而我不讳言,初令我来此时,是颇有点不开心的。倒不是因为其他,我这样一个沉默的人,置身陌生环境,常常会手足无措。那种感觉,真是不好受。
七月四日,小雨霏霏天,我不到八点就到了都府堤。等了一会儿,开门的阿姨才来,我过去问,才知道当天闭馆,但只简单说明情况,她也很和善的让我进了。一进院子,是大片的青翠草坪,红褐色的柱子,青砖黑瓦,繁茂的悬铃木和香樟树在滴雨,青石板湿漉漉的。院里静寂无人,细雨湿流光。我一个人慢慢走了一圈,心想,也许这里还不错啊。
临时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我用抹布擦了桌椅和电脑,草草打扫了一下,便很快开始工作。是给需要的资料分类编目,并做尽可能详细的说明。“大雨暂歇,一日枯坐,纸张翻飞如雪片,四围静寂幽长。要整理的资料绵延数十载,纸上涉及地方南北贯通,一翻便是一个十年,而我亦仿佛经历了一场历史的游走。”这是当天的日记,明显笼罩着一种孤独的情绪。然而,很快就不只是孤独了。
七月六日,一早醒来,发现大雨倾盆。我多数时睡眠颇佳,常常醒来就是天亮,因此以为是夏日常见的梅雨。撑伞走到半路,水已没过脚踝,路上不少人都赤脚淌水。我本想偷懒,后来还是折回去,换了拖鞋。事后证明这一决定是十分正确的。
到都府堤巷口,才发现这里淹得更厉害。我起初还有一丝兴奋,很豪气地挽起裤脚趟水,走到街中,水已没膝。遇到全副武装的三位工人,他们在检查窨井盖,奇怪地看着我说,小伙子回去吧,前面越来越深了。我想,到门口了,总要去看看的。捡了一根漂浮的木棍探水,越走越慢。有一刻,水渐渐没到腰,心中开始觉得恐惧,四顾无人,只有浸泡在水中的车闪着昏暗的光。我趟水到馆门口,才知道已闭馆,又继续出来;雨没有丝毫退步的意思,伞在它眼中已成玩具,左右飘摇。我浑身透湿,又冷又饿,走到附近的户部巷躲雨,艰难地吃了一碗热干面。
同事告诉我,都府堤的公园曾是一个水塘,地势低洼,所以容易积水。后来看新闻,才知这一夜暴雨不止,城区尚不是淹得最厉害的,吾乡新洲凤凰、三店正面临溃口之险,隐约有九八年发大水的架势。彼时,我不到九岁,除了父亲早出晚归抗洪,及不必去上学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外,几无记忆可言,而这一次是实实在在的经历。没敢把这告诉母亲,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写“有生之年,都难忘今日。”
七月七日晴。都府堤齐腰深的水已退去,但馆中损失严重,一楼的电脑、桌椅和书籍等物品被渍水泡坏,因担心漏电危险,电路也不敢开通。连续几天没有电,我回归手工时代,先手写资料。雨时断时续地落,馆中人大概都在清理物品,书籍浸湿的太多,摊开一些晾在我所在的办公室里,散发出淡淡霉味。我把窗户和门敞得大开,院中湿漉漉的幽深迫不及待地涌入。
休息时,看包里带的余冠英版《诗经选》,读了十几首,颇喜《邶风·绿衣》中“絺兮綌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句。春秋战国时代,诗常用于外交、祭祀、宴饮等场合,引经据典是当时常态,故而容易断章取义。“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原是丈夫思念故妻,但单拎出来看,实在有沟通古人、知音相惜的意思,且这意思比原意还更打动我。这与王国维抽离宋词句,阐述人生三境界颇相类似。
那几日心中惴惴。下班特意去走长江大桥,在桥上看长江,平日温顺东去的江水,如狂暴的兽向两岸疯涨,江水与马路齐平,才真切觉得王湾“潮平两岸阔”的“阔”字下得惊心。好在,雨季慢慢离开,夏天终于来临。
七月中旬的时候,去北京出差,是平生第一次去京城。匆匆两日,忙着办理手续材料,哪里也没看,唯傍晚去了一趟北大。与炳辉约定在北大西门见面,在人群中,我一眼就捉住了瘦高的他,“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笑着说。他带我看了图书馆,在未名湖畔闲走,去看了找了好一会儿的中文系和历史系楼,聊少年的往事,谈起将来的打算。天慢慢地沉下来。北大校园中有许多槐树,白而碎的花,在热风中落了一地。
自京归后,日日在修改资料目录,一条条查找,才真切体会到历史资料的尘封与真伪难辨。无论掺杂何种心态,对一个时代历史的故意忽视,甚至取回避态度,均是很不该的。个中原因,除却客观环境限制,应该还有对于“史”的认知。但民国时代,孟森研究清史、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史所得之卓越成绩,于通达的史观而言,应是极好的例证。我慢慢查,一点点开始尝试理解。门外木叶幽阔,蝉鸣肆无忌惮,日头从叶间泻下,仿佛是白丝。
都府堤旁边即是户部巷,五分钟的路,我常常中午走过去吃一碗糊汤粉,加一份豆皮,典型的武汉吃法。办公室还没有打印机,有时需要打印文件,便去隔壁的办公室求助,都是微微一笑,很和善的。有一天中午实在嫌热,到户部巷买了饭带回来,门口遇到隔壁办公室的姑娘。她问我,怎么不在食堂吃,又聊到资料收集整理情况,云云。才知道原来是同龄人,历史系,一瞬间就觉得自在了许多,就这样站在走廊里聊了很久。
午睡时,迷迷糊糊中听到窸窣声,勉强睁眼,竟然是一只黄鼠狼在桌下觅食,扬着硕大的尾巴。我猛地跺脚,它楞了一下,才飞似地夺门而逃。我还是很小的时候见过此君,常常偷吃家中的小鸡,是乡下人人喊打的家伙。然而,能在城中见到,真是意外呀。
天一日热过一日。七月二十八日的晚上,我为了凉快,新买了一床竹席。清代顾禄《清嘉录》中说到纳凉,有一段很喜欢:
纳凉,谓之乘风凉。或泊舟胥门万年桥洞,或舣棹虎阜十字洋边,或分集琳宫、梵宇、水窗、冰榭,随意留连。作牙牌、叶格、马吊诸戏,以为酒食东道,谓之斗牌。习清唱为避暑计者,白堤青舫,争相斗典,夜以继日,谓之曲局。或招盲女、瞽男弹唱新声绮调,明目男子演说古今小说,谓之说书,置酒属客,递为消暑之宴。盖此时铄石流金,无可消遣,借乘凉为行乐也。
泊舟斗牌,听曲说书,旧时江南消遣暑天的风致,现今已毫无踪影。只有傍晚随处可见的广场舞,日复一日俗滥的嘈杂声,我每回经过,心里都一阵阵紧。倒是都府堤的树荫下,每日清晨有中年男女踢毽子,四人一组,红色的毽子,翻飞若风中花落,煞有可观。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积玉桥这一路有几株颇大的银杏,间隔在樟树中。我忘了在哪本书上读到,说银杏亦叫公孙树,往往爷爷辈种下,要到孙子辈才会挂果;但积玉桥真有结果的银杏,与其他的差不多高,却独独挂了果。果与叶颜色相同,仔细看,会发现如鸟卵般大小的果子,齐齐藏在叶间。树下行人匆匆而过,我在树下看了一会儿,很想摘一串,又够不着。
又一天中午,突然想起江滩院子里的凌霄花,很不好意思地托同事思敏君拍了几张照片。大概因了那首著名的《致橡树》,凌霄花并不怎么受欢迎,也似乎不很为人知,但我却极喜欢。它即便是攀援,也是默默的,花红得也不张扬,烈日下一壁幽绿如帘垂,自然而然的,是很美的景色。
从大雨倾城,到烈日似火,我在都府堤也有一月了。去年的此时,我尚在山中,之后到江滩边,如今又暂歇都府堤。苏东坡有诗道,“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可是,我哪里有这般旷达,如同想念江滩边的生活,明年的此时,大概我亦会怀念在都府堤的日子。
记得《圣经》中的一句话,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而我也只能拉拉杂杂,写写这七月的故事。无事便是心安呵。 (作者:甘超逊 ,此文发表于2016年第三期《艺术》杂志)
上一篇: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下一篇: 百年中山大道华丽转身

![]() 办公室电话:027-82812716
办公室电话:027-82812716
![]() 值班电话:027-82834953(夜间、节假日)
值班电话:027-82834953(夜间、节假日)
![]() 档案馆查阅咨询电话:027-82812709
档案馆查阅咨询电话:027-82812709
![]() 展览参观咨询电话:027-82784374
展览参观咨询电话:027-82784374
Copyright © 2020 武汉市档案馆 版权所有 湖北省武汉江岸区怡和路59号
鄂ICP备19019621号-1
 鄂公网安备 42010202002201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202002201号


读档

武汉档案